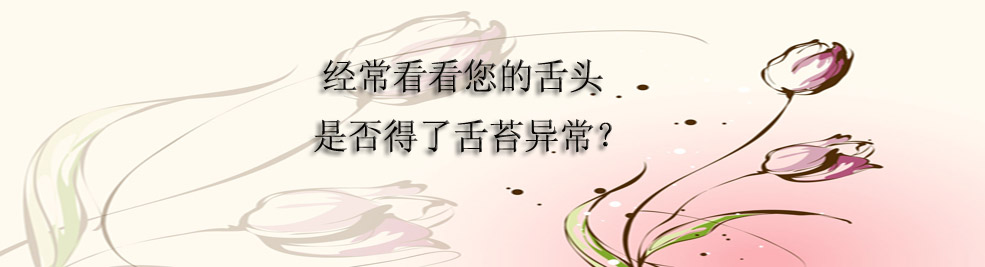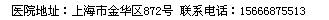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舌苔异常 > 病因探究 > 午夜小说雪夜
午夜小说雪夜
康信德,原名邵风,年12月17日出生于安徽肥东八斗镇,诗人、作家、编剧、制片人。16岁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创作短篇小说《斜眼狼》、《金钱记》、《卖鱼》、《马德先生》等等;长篇小说《桃金娘》、《秋娘》等;文学剧本《罗莹》等;《出租房》等;长诗〈贾佑思历险记〉等,以及大量抒情诗歌及文学评论;年担任《小说时代》执行主编;年创作影视50集剧本《疯狂家装》,同年该剧全网上线发行。年创作短剧《逗你玩》系列、电影剧本《出租房》、《野人谷》等。读后感杂志签约作者。;13
一
一会儿,她走下床,拖着粉红的虎头鞋,走到柜台取些暗红色的酒瓶,侧过头来问我:“来一些吗?”我望着她天鹅绒睡裙下那双白净修直的腿,心不在焉地回答:“要一些。”她将葡萄酒倒进高脚酒杯里,又取出白酒掺和进去,晃了晃,对我说:“恩,要这样会才好一些,有劲!”我忘乎所以,以为她这样做是为了好好醉一顿,配合这儿情调,在这个不足三十平方的舒雅的厢房里只有我和她。青灰色的床被、浅粉色的毛毯、两个海蓝色抱枕和一只毛茸茸的棕色大狗熊。她跟我说过,她喜欢晚上抱着这个大狗熊睡觉。在床头上,还挂着一对粉红茶花簇成的布草莓。她说过她十三岁开始就懂得装饰自己的“窝窝”,眼前这个清爽、淡雅、干净的闺房就是她设计和装饰的。
“我喜欢听到你睡觉的鼻鼾声,它证明你睡着了,人睡着了就像婴儿一样!”她走到我身边,坐在旁边的木藤椅上,下意识地将腿翘起来。我望着她的曲美的身体,思絮翩翩。
“不要这样不礼貌,小家伙!”
因为我比她小,所以她总以小家伙来昵称我,其实我已经二十二岁了。尽管我刚从大学毕业,踏入社会不到半年,看上去确实像个毛糙的家伙,但是我的全部器官都已经成熟了,而且,我下颚长着髭须,这在古代可是美男的表证。也许我可以不修边幅,但我是经常修理胡子的。再说,我的脑袋像哲人一样善于思考问题和幻想,我还是海德格尔的信从者,誓言要毕生追求诗意的生活。而此刻,眼前这个天使般的女神,她却经常用“小家伙”来戏称我。有时,我真想像做个“终结者”,扛着一杆枪,像史瓦辛格摆出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派头来。而那时,眼前的小女人,定然会像小鸟依人一样偎在我胸前。于是,我们一起接受爱神的扫射。在爱情的征途,我甘愿溅洒生命最后一滴血。
“你再这样看我,就不理你了!”
她故作愠色低下头,独自饮酒,酒刚到嘴边,突然她爽朗地大笑起来。
“我们这是在做什么?”她说,“我可是你姐姐啊。”
我不爱听到她这样的话。大概在七年前,我们成了邻居,那时她正上高中。那时,我们相处的不错。一直以姐弟相称。后来她考上了新疆石河子大学,从此我们几乎没再见面。再次见面是前几天我在九狮公园闲转的时候,碰到她独自一人坐在垂柳下的凉椅子上。她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而我也是小伙子了。见到她,我重新燃起来少年时代对她的渴望:想她做我的女人。而现在,我似乎正扮演着情人的角色。但她恋爱了,我知道;而且,我还知道那个家伙家里条件很好,他姐姐嫁给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他自己是个小老板。具体做什么,我没有 “在枝干粗壮的树下,一卷诗抄,
一大杯葡萄美酒,加一个面包——
你也在我身旁,在荒野中歌唱——
啊,在荒野中,这天堂已够美好!”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鄙夷哥哥的思想观念。我觉得他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沉沦到飘渺的情爱之中。而且,哥哥最近几年跟爸妈关系很不好,家人希望他们夫妇留下来不要到新疆去,而嫂子在家是个孝女,舍不得丢下年迈的父亲和还未成亲的弟弟。因为爱情或者说因为女人,哥哥毅然决然去新疆并留在那里。因为这个我一度认为哥哥是个偏执狂,是个爱情疯子。不过,现在我却想念起了哥哥来。……也许,当一个人寂寞的时候,任何亲人想起来都是那么亲密,那么和善,那么可爱。可一当跟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却又是那么无缘故地厌烦他们。
六
窗外风声息尽;一向喜好发出沙沙低鸣的香樟树呆立着。远远的,倒是奇怪地传来“咯吨、咯吨”的野鸟声,这样的叫声在夏日的乡村最为常见。大概因为鸟叫的缘故,夏天那种暖烘烘景气逆袭我。家中的空调坏了,唯有一台取暖器还能用。我横躺在沙发,盖上厚厚的米黄色的毛毯,手里拿着一本《海德格尔选集》上册。——我不知不觉睡着了。没有多久,只见眼前出现远连绵不断起伏的丘陵,忽然,丘陵变成陡峭的山林,到处是忽忽飘倏的雪,一转眼的工夫,地上的荆棘只能见到一些梢末。我孤零零地被置身于风雪中,开始什么也看不见,只见大片大片的雪花在我脸皮飕飕地下着。忽然,一只失群的天鹅拼命地扑着翅膀,两只血红鹅努力弹着雪块。它在逃命。在天鹅后面一只黑毛猎狗正在追赶。很快,猎狗咬住了天鹅的脖子,天鹅狂乱地挣扎着。就在这时,我听到一声枪响,黑忽忽的子弹从我眼前飞过。接着狗中弹了,被击中了后臀部,狗“汪汪”叫着跑开了。我赶紧朝天鹅跑去,可我到那时天鹅已化成一摊血,沉浸到厚厚的雪层里。没一会,从血迹里迅速地长出一枝玫瑰。玫瑰在风雪中摇曳一阵就凋零了,接着,雪把玫瑰盖住,四周重又皑皑一片。我茫茫然地看着眼前神奇的一切……。
半夜两点多,放在口袋里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手机铃声每个一分钟就“嘟”的一下。我是个对手机信息很敏感,即使在睡着都会因为那小小“嘟”声而惊醒。短信是林雪娇发过来的,而且是一条彩信,配的是雪人图。
“你睡着了没?不好意思,我想你现在应该睡觉了。下雪了,我睡不着,我在河畔的凉亭里,看飘雪,感觉真的很不错。”
看雪?……我掀开窗帘,哇噻,外面果真是下了很大雪。窗台上都积了10公分厚的雪。这是今年的第二场雪,上一场是赶在圣诞节那天下的。那一场只飘了两三个小时,但因为地温比较高,雪落地就成水了,几乎没有什么积雪。不过,此后的天气一直就不怎么好,且一到晚上就阴冷的很。看今晚的气温,估计要零下七八度。——“这么晚,这么冷还在看飘雪!”我担心她会做出傻事,赶紧拨通她的电话,电话通了,但手机一直都没有人接。我更担心了。
“这家伙不会干什么出格的事吧!”
我一骨碌从立马从沙发上跳起来,马上披件呢大衣外套,风风火火地朝她说的风月凉亭急奔而去。从我家到新修公园的风月凉亭有两里路。一路上我不停地拨打她的电话,但一直没人接。我非常慌张,顾不得没在雪层里的小路多坎坷,顾不得我的脖子里被雪花灌满,顾不得多次不小心而摔倒在地。我着急且恐惧着。——直到我快到凉亭了,她才接我的电话。
“你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接电话?”我脾气不得不坏。她的回音很小,像一点力气也没有。
“我快要死了!”
我迈开步子朝风月凉亭狂跑。——“但愿她没事!”——我跑到她的身边,她倒在凉亭的角落,头发蓬乱,身边还放了几个啤酒瓶。她的手凉凉的,嘴冻的说不出话,直哆嗦。
“你怎么这样?你疯啦!”我一面抱怨她,一面立马脱下大衣将她紧紧裹住。因为她体格比较大,我无法将她抱在怀里,只好将她背起来,然后一边不停地跟她喊话,一边粗喘着气往我的家赶!
七
快到家门口的时,医院,因为她在我身上一动也不动,我怕她冻坏了。可我掉转方向,医院路线时,她在我耳边轻声细语地说:“回家!——回家!我想回家!”她每说一句都越发脆弱。
一进家门,我就将她轻轻地放进被窝里,用干毛巾将她衣服上潮湿的部位整干,并用羊毛大围巾将她腰下部裹住,然后用羽绒将她浑身盖着,上面加了两层大毛毯压紧。我将电暖器放在床边,把温度调到最大瓦。从阳台里照了一些木炭。以前每年冬天,父亲都喜欢烘碳火。空调彻底坏了;阳台的窗户也太大,关不严,寒风能从罅缝里钻进来。不能开窗户,可我烧起的碳却不是无烟的,很快就熏烟四起。真是没有生活经验害死人呢,我自己都呛的难受,真想将玻璃砸了。我不停地扇烟,还不忘记将碳火用脚跺灭。折腾了好久,房间才暖和一些。
她一直在昏迷之中,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因为冻坏了。不过,她的脸色渐渐变的红润了,呼吸也开始均匀起来,青嫩发红的胸房随着呼吸上下起伏着。我想,她应该是没有事。我拖了一张沙发椅子过来,然后,躺在沙发里,用一床小被子(侄儿在家时用的被子)将自己双腿和腹部盖着。窗外,风雪怒号着,街道、房屋、香樟树、桂花树、松竹都哑然不语。
我静静地看着她。幸福,有时候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它只存在于舒心阔怀的观望中,甚至不能粗声提它一下,不然,它宛如击破的水影,会顿时消失。
我的眼前浮现哥哥的狡黠的笑容;我的耳边听到父母的谈笑声。我甚至能看到灯火辉煌,红字飘飘。我的手开始温热起来,渐渐汲着一些汗。有什么喜事在等待我吗?——我的耳根发烧。“如果一切都是可能的,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便可以和她这样温存地生活在一个狭小的二人世界里。我呢?是真诚的。”我得意着,俯下头,将她的手轻轻放在我的脸上;她的手指间散发着幽兰花的清香。
……窗外的雪已经下的很厚;外面银光一片。
“如果可以,我带她到别的城市里去一起生活,去上海或北京。我舅舅在上海,北京也有我的同学在那;而且,北漂的不错。”这样想着,我下了沙发椅。脑子下意识地走到哥哥的房间,从哥哥的书柜里翻他东西,一会儿我翻出一本薄薄的腊黄封面的诗集,是蒲宁抒情诗选《夏夜集》。对诗我没有研究,不过还有点喜欢。“这样的时刻,总得读几句诗似乎更恰如气氛。”我自言自语。但脑子老是浮现另外一些婚庆的场景。我再次轻轻抓住她的兰花指。“我爱你!”我对她耳语。她的红润的脸蛋埋在蓬乱的长发里,睫毛整齐,饱满的嘴唇似乎微微地向上翘着。吻她的冲动侵袭我;当我把嘴靠近她嘴唇上部时,迅捷地吻了她的鼻子。
时间到了零晨四点。忽然她开始说起了胡话;她的头好烫。
八
我跑到小区外,找了一家还亮着红“+”字小灯箱诊所。我朝着诊所刷过新漆的铁窗敲打着,叫喊着有没有人。过了十几分钟,诊所里的电灯才亮起来。这个诊所医生我认识,按辈份我要叫他大伯,以前是个军医。他头顶毛发早已稀疏,鬓发也白了;肥胖的脑袋,耳朵像猫耳一样薄而尖小;保留一嘴老旧而整齐的牙齿。他说话的声音沙哑无力,大概因为这个因素,他努力通过憨诚的微笑来弥补给人的不亲和感。他见有人敲窗,就职业性地披上了白大褂,然后才开窗。
“……什么情况?”
“大伯,是我?”我递上话。“有人发烧了。”
他戴上老花镜子,贴近我看。
“是你啊;发烧了?!”他习惯性转过身要拿药。
我急了。
“大伯,你怕要到我家去一趟;不是我发烧,是雪娇,就是林志平的女儿。”
“老林的女儿?”老医生惊讶起来。“他家不是搬新城去了吗?”
“哎呀,没时间解释那么多了。你带上药箱到我家来一趟,可好?雪娇烧的很厉害!”他漫不经心地去拿药箱。“老伯,快一点啊。”
过了两分钟,他才从家里出来。
“就发烧?什么时候发烧的?”
我搀扶着他,路滑。“你小心点!”
“我先去看看;她家还没有搬吗?不是新买了平方米的复式楼吗。——她爸爸前几年生意做的好。……我有半年多没见到林志平,这老家伙以前常到我家来喝酒;前段时间听说他们去了马尔代夫旅行。”医生不停地数叨着。诊所离我家有三四分钟的路程,加上雪滑,要多用三分钟。到了我家后,我把正在冒虚汗的林雪娇扶了起来,然后给她垫了个大枕头。雪娇还是半昏迷着,眼睛没有力气睁开。老医生让我站到一边,他来给林雪娇看量体温、舌苔、把脉。前后二十多分钟,然后才跟我说不要紧,可能是着凉冻的,女孩子家身体虚弱。我上前,将雪娇重新盖好;并将烧的发红的取暖器降了瓦。这时,老医生从要箱里拿了几片退烧药。我问他还要不要吃别的药,他说不用了,吃了退烧片就可以。并让我烧点开水,用温水喂她喝药。我按照吩咐,一一照做。
忙完后,我来到客厅,为老人切了一壶清茶,请他在客厅坐坐。老医生露出一股神秘的微笑。不用猜,他是在琢磨我跟林雪娇的关系。我努力保持镇静;以表示我跟雪娇只是普通关系。或者说是邻居关系。以前她家就住我家隔壁的隔壁,都在一个楼道上。前段时间她家老房子准备卖,但至今还住着。老医生家以前就住在我楼上;我们也算邻居。老医生的儿子跟雪娇是初中同学,但他儿子现在是个军人,据说还是一名上尉。
“雪娇这丫头,怎么弄成这样?”医生吹着茶叶。
我忙提起水壶,给他继续添开水。
“跟人喝酒喝多了。”我回答的干净利索。
“……那像她爸,没事总爱喝两口。”他嘿嘿地笑着。
我火热的耳根,本能地防御着他套我的话;我叉开话题。
“今年雪很大啊;好多年没见过这样大的雪。”
“……物价又要上涨了,我刚才还在床上跟你伯母说这个事,……”
我得意着;因为我叉开了话题。
“还能涨多少吗?”
“恩,至少翻三翻。”老人挥动着右手,翻穿转了三下。“昨天大包菜一块二;今天早上看,非卖四五块不可。我消息灵通,每天都中科医院曝光中国白癜风治疗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