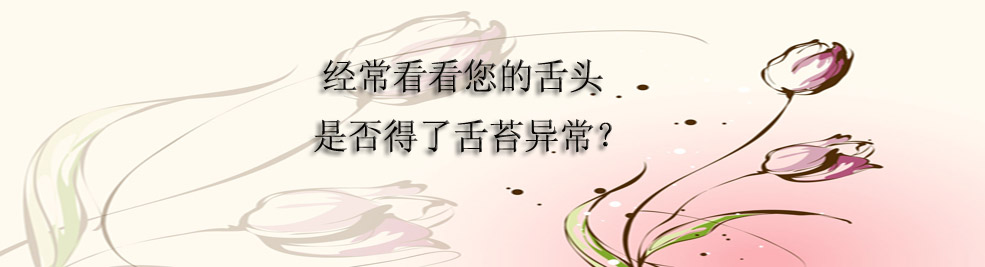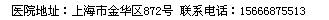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舌苔异常 > 预防治疗 > 再发现张楚旅行短篇节选
再发现张楚旅行短篇节选
再发现
旅行
张楚自在说
孤单的旅程
□张楚
我一直想在朋友们中间组织一个“读书会”,每个月和朋友们携妻带子,到郊外或者到茶馆,一起读读书,谈谈生活和理想,让我们过于绷紧的精神和焦躁的情绪有一个小小的缝隙。我想让我们的精神世界丰沛一些,充盈一些,神圣一些。也许臆想中的此举,只是我妄图反抗县城粗俗生活和旺盛欲望的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在我的朋友眼里也许是可笑的。或许真的就是可笑的吧。这种活动只适合的艺术家和大城市的文艺青年。在小县城里,是无所谓神圣、无所谓精神的。西蒙娜·薇依说:“神圣在尘世中应是隐蔽的。”那么,我尽管让我小小的愿望隐藏起来好了。我该做的,是在小县城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然后在午夜十分,让我腰间盘突出的身体回归书房,静静地与另一个我,另一个纯净的世界,开始漫无边际的对话、旅行和嬗变。
小说
1
关于奶奶和爷爷的那次旅行,兆生想是件蓄谋已久的事情。在他们多年的乡居生活中,他们仍与外界保持着疏散而温暖的联系。他们有一台15英寸的黑白电视,每天晚上七点,奶奶把电视打开,戴上花镜看《新闻联播》,当然,他们对各种性质的战争和会议、出访和丧礼、奇闻逸事和反腐形势从不感兴趣。他们酷爱这个栏目,只是因为他们喜欢那个一只眼睛单眼皮、另一只眼睛双眼皮的女播音员。她和他们的大女儿长得像极了。每当她张开嘴巴,从洁净的牙齿间蹦跳出一桩桩国家或国际大事,奶奶总会微笑着对爷爷说,瞧,咱们草莓又开始上班了,她可真准时啊,一点都不偷懒。他们的大女儿草莓,在前年的春天喝敌敌畏死了。
他们出发的那天是农历三月初二。爷爷四点钟就爬了起来。那个早晨,爷爷觉得空气通透清亮,韭菜花的甜味不时刺激着鼻孔,所以等他端着一笸箩嫩草喂毛驴时,他开始吹起了口哨。太阳不久就拱出来,猪圈上的倭瓜花蕊栖息着一只熟睡的知了,爷爷还在葫芦秧上逮着了一只蝈蝈。这只肚子滚圆的昆虫让爷爷愣了一会,他摸了摸它的翅膀。它翅膀上绿色的花纹湿漉漉的。
奶奶对于爷爷的这次决定,开始时极力反对。他是越老越糊涂了,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脑筋要是转不利落,才最伤神。当她倚在门框招呼爷爷吃饭的时候,爷爷正在给那辆老水管自行车打气。她扯着嗓子嚷道:“吃饭了!你除了会折腾人,还会做点啥?”
后来当他们把门锁好时,奶奶盯着墙角的那丛樱桃树,说:“我不去了。我的关节炎又犯了。”
爷爷对奶奶的变卦在意料之中,对于她习惯性地拆台,他已习以为常。他把老水管自行车靠在墙壁上,走到她身边说:“你以为我离不开你?我没有你照样能活!”
奶奶噘着嘴蹭上了他的自行车。她叹了口气,粗糙的手皮抚摩着无名指上的那只铜戒指。
爷爷驮着奶奶朝村南行进。五月的村庄,牲口早早苏醒了,那些在村头巷尾嗅来嗅去的狗尾随着爷爷的自行车小跑。它们红色的舌苔冒着哈气,慵懒而顽皮。另外他们对在村头遇到周德东也没有感到奇怪。周德东每天早晨四点半到村头等人已经是周庄最著名的事件。远远地爷爷下了自行车,和周德东打着招呼,“我说他二舅,还在等国庆啊?”
周德东是大儿子媳妇的哥哥。他呼噜着嗓子点点头。周德东的脑瘀血已八年了。他的嘴巴被拴住了,说话不利索。对于爷爷殷切的问候他很开心。他指指爷爷,又指指奶奶,问,“你们老两口……这么早……去赶集啊?”
爷爷摇摇头,去看奶奶。奶奶对周德东说,“你怎么老有操不完的心呢?还在这里傻等什么?你儿子早不从这条路上过了!”周德东的儿子和周德东打架,搬到他丈母娘家,九年没踢过家里的门槛了。不过他到轧钢厂上班时要路过周庄。周德东便天天跑村头来等儿子。对于这种徒劳的等候周德东保持了一个周庄人应有的耐性。可他一次也没有等到。
对于奶奶嘲笑式的诘问周德东保持了惯有的冷漠,于是爷爷和奶奶的自行车又出发了。奶奶坐在车后,胳膊上挽着一个黑色包裹。对于这个早晨的周庄人来说,爷爷和奶奶的这次旅行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很多周庄的人,在这个闪着阳光碎银子的早晨,看到了两个老古董,被一辆会唱歌的老水管自行车牵引着,晃晃悠悠驶出了周庄。
2
爷爷怎么想起要去十里铺看海呢?奶奶觉得是那台黑白电视机造的孽。电视开始时,那个戴着眼镜、富态的政府官员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讲话,讲得好好的,不知怎么就没了,电视里好多人在一座山上挤,然后是公园、商场、故宫和草原。播音员用充满激情的声调宣布,五一黄金周又来了,国内游客坐着飞机、火车、轮船和大巴去旅行……奶奶以为爷爷早睡了,他对电视从不感兴趣。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他也不赞同她看电视,要不是因为那个像大闺女的播音员,他准会一棒子把电视砸了。他的耳朵虽然佩戴着助听器,她说的十句话,他大抵只能听到五句。奶奶没料到爷爷突然从炕上坐起来,抻着奶奶的袖口说:“明个我带着你去十里铺。我还没去过十里铺呢。”奶奶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去十里铺做什么?爷爷把嘴巴贴在奶奶的耳朵上说:“我带着你去海边走走。你这么大年岁了,还没看到过海呢!”
奶奶后来坐在爷爷的车上,后悔万分。她首先是替爷爷担心。十里铺离周庄有一百里路呢。他这副老骨头,骑自行车能扛得住吗?后来她咬咬牙说,你要是真想去,我们坐公共汽车吧!十块钱一张票,能买二斤猪肉呢!我豁出去了!爷爷摇头,奶奶就说,来回也就四十块钱,是四十块钱重要呢,还是你的老命重要呢?爷爷还是摇头,奶奶嗫嗫地说,庄里人要是知道我们跑这么远去看狗屁的海,还不得笑掉大牙啊?
奶奶见爷爷没吭声,而是走出了屋子。奶奶这才恐慌起来,她知道爷爷生气了,生气时爷爷通常的做法是和她分居。去年夏天他就和她分过一次。他在屋顶搭了一栋木房,那些天,每当夜色降临蚊虫四起时,爷爷扶着梯子爬上墙头,像壁虎一样蛰居到他的木屋。从此他便和奶奶分居了。这件事让奶奶哭了好几天。那个夏天,每当繁星在夜空撒开,爷爷就像一只迟钝的大鸟飞上屋顶。他的动作在长期的攀缘中趋于完美,后来,他只需要马夫钉一只马蹄的时间就能顺利抵达他栖息的巢穴。还好,小雪到来时,爷爷自动从房顶撤离,最后一个清晨,他从屋顶迈到墙头,然后像一只悠闲的蝙蝠飞下来。等他落到地上,他的脚踝被蹾了下,于是他对奶奶说:“哎,我真的老了啊。”
老了的爷爷驮着奶奶过了李庄和夏庄时已气喘吁吁,奶奶说,你要是累得慌我们就歇歇吧。爷爷没听到。他的身子佝偻着起伏。他瘦得让人心疼。参军前他替地主扛活,是最出色的雇工,年辽沈战役,他用刺刀捅死过两个国民党士兵,年抗美援朝时他是炮兵,轰死过六个美国鬼子。可现在他的身子骨轻得犹如一把干柴。
“你没听到我讲话啊?”奶奶有些生气地说,“我想解手!”
爷爷这才从自行车的前档迈下来,把自行车扶稳当,奶奶小心着着地。奶奶看了看爷爷说:“我们回家。”
爷爷说:“米家?米家村离这里还有四里地呢!”
奶奶对爷爷的打岔已经麻木了,对一个耳朵聋的人生气是不值得的。她再次扯着嗓子嚷道:“我要回家了!我不去十里铺了!”
奶奶讲完话时马上低下头,有辆摩托车从他们身边蹭了过去。骑摩托车的是个中年人。她一眼就认出他是谁了。她转过身子,假装和爷爷说话,她的嘴唇轻轻地翕动着,可是她确实什么都没说。
“你不舒服啊?”爷爷大声地说道,“你哑巴啊?吭声啊!”
他们嘈杂的声音还是把那个中年人吸引过来,这样,在他们旅途的开始,奶奶遇到了她最不想遇到的人。在奶奶多年的乡村生活中,有两种人最让她憎恨:一种是偷鸡摸狗的人,譬如周庄的村书记周卫星,周卫星每年春节都从村里划拨二十块钱给爷爷奶奶,但奶奶从不正眼瞅他,就是因为周卫星和村里的会计王秀珍有一腿;另一种人便是“伙混”。“伙混”是这里的方言,说白了就是汉奸。奶奶打日本鬼子时是这一带的地下党,还兼着周庄的党支部书记,那年月,她除了给上边秘密送情报,组织村里的媳妇们给八路军纳布鞋,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如何应付那些“伙混”。而这个骑摩托的中年人,正是当年这片“伙混”头目刘三会的儿子。刘三会“三反五反”时被枪崩了,可他的儿子还活着,而且活得挺滋润,养着“解放牌”卡车,还是县里的人大代表。平时他胸前总挂着一张“人大代表证”,即便是在三伏天,证件也用铁夹子在背心上钳固着。他的这个红色的标签已经镶嵌进肉上,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中年人双腿哈在摩托车上说,“周大叔,你们这么早,有急事情吗?”
无疑这个中年人认识他们,不仅认识他们,还很亲密的样子。爷爷没认出他,憨厚地笑着。
“要是有急事,我驮我婶子一程啊?”
爷爷没有听到他说什么。奶奶则绷着脸说:“不用!你忙你的吧!”
中年人很快消失在庄稼地里。奶奶突然觉得,这是个多么让人伤心的早晨。她以为一辈子也不会遇到这些她厌烦的人了,她已经四年没出过周庄了。她是个懂得记恨的人。奶奶是这么想的,一个人要是一辈子连个记恨的人都没有,那也就白活了。
这样,奶奶和爷爷的旅程在太阳升得一指高时受到了打击。她看到村庄的烟囱里都冒出了灰烟,而陈年的麦秸垛里不时游走出一条青色小蛇。路过米家村时,有辆公共汽车从爷爷的身边呼啸着滑过去。奶奶从背后捶了爷爷一拳。爷爷扭过头说:“你累了?累的话我们先歇息一会儿。嘿嘿,你的骨头,终究没有我的骨头硬朗呢。”
3
对于米家村这个村庄,他们都有些陌生。这个村人少,也没他们的亲戚。后来他们在一家小卖部门前停了,和那户人家讨水喝。对于大清晨这两位有些鬼鬼祟祟的不速之客,女主人显得缺乏热情。她一边打着哈欠一般嘟囔着问:“哪个村子的啊?”
“周庄。”奶奶说。
“哦。周庄。”媳妇拢着乱糟糟的头发,顺脚踢了踢那只白色哈巴狗说,“你们进城吗?怎么不坐公汽?”
奶奶仔细端详着这女人。她的眉眼略发红肿,说话时牙齿兜不住风,因为她缺颗门牙。奶奶便问,“米小翠,你那颗门牙怎么还不补?吃东西能得劲吗?”
显然女人对奶奶唤出她的名字很吃惊,她认真地打量着奶奶,半晌才野鸭子似的嘎嘎笑将起来,她的笑声感染了爷爷,他被这个女人的好客打动了,于是他说,“东家,给口水喝啊!”
女人说:“这一大早,你们是干什么去啊?日头还巴巴地矮着呢。”
奶奶有些支支吾吾。米小翠是草莓的初中同学。“还没吃过吧?我煮把米,你们吃了再走啊!”
米小翠仍拢着头发说,“哎,草莓怎么那么想不开呢?有福不会享,喝的哪门子的敌敌畏呢?”
奶奶的脸变红了。对于大女儿的自寻短命,一直让她羞于启齿。这丫头当了二十年的民办教师,前些年民办教师转正的时候,没评上,就喝了半瓶敌敌畏,死了。
“多好的一个人啊!”米小翠捏着根笤帚苗剔着牙齿说,“能说能唱的,两孩子那么小,就舍得下撒手不管,哎,也是个狠心的人哪。”
奶奶拉着爷爷的袖口径自出了小卖部。爷爷本来还咕咚咕咚灌着凉水,他把水瓢扔进缸里。刚才他也听到米小翠的话了。他的耳朵总是在不该听到声音的时候变得像野猫那样敏锐异常。
奶奶和爷爷离开米村时,奶奶还在流着眼泪。她记得她好几年没哭过了。米小翠在他们离开时很热心地往奶奶怀里塞了几个面包和两包榨菜,被奶奶偷偷扔在庄稼地里。
米庄离他们越来越远,太阳已升到两指高。天空爬着灰色云朵,鼻孔里不时嗅到桃花浮动的暗香。前面一定是菜庄了,菜庄有一百亩桃树,每年春天,十里八里的地方都能闻到那种让人骨头发软的香气。奶奶的心情突然好了起来。她看到那个邮递员骑着绿色的邮电车朝这边慢腾腾地走。在半路上遇到熟人是件多么开心的事情。奶奶兴奋起来,她探着脑袋喊:“大侄子!你这是去哪庄啊?”
那个邮递员戴着顶绿帽子,虾米眼珠吧嗒吧嗒地眨着。很显然,他在这里遇到奶奶很是吃惊,他细声细语地说:“你的补助还没来呢。你们这是去看亲戚吗?”
奶奶非常喜欢这个羞涩的邮递员,他除了有个细长扁平的脑袋,还配了两只幼小的耳朵,看上去就像一只草地里满腹心事的蚂蚱。奶奶从来没见过这么丑的人,每回见到他都觉得很亲切。平时都是这个邮递员给爷爷和奶奶送补助,爷爷是十五块,奶奶是十块。领补助是奶奶最得意的事,村里就她和爷爷领补助。他们是村里资格最老的党员。
“我和你大伯去十里铺啊。”奶奶有点自豪地说,“我们嘛,去海边子转转。闲着也是闲着。”
“哦。那边有亲戚吧?现在海上正是上货的季节呢!面条鱼和虾爬又肥又便宜。”邮递员舔舔干迸的嘴唇说,“如果方便,给我带两斤面条鱼回来啊?”
“好啊好啊!”奶奶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邮递员开心地走了,奶奶对自己态度的转变感到很诧异。她刚才还想和爷爷分道扬镳,怎么一会态度就变了呢?她有点生自己的气,她对爷爷说,“我们不去十里铺了,我们去解放那里吧。我想解放和兆生了呢。”
解放是奶奶的大儿子,兆生是奶奶的大孙子,他们都在县城工作。去十里铺要路过县城的。解放是县工商局的局长,天天忙着开会,兆生在税务局上班。“老儿子大孙子”的俚语还是对的,奶奶最疼的便是兆生。
爷爷没有吭声。对于奶奶的絮叨他抱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在这个春天,他看到了绿庄稼、看到了桃花,而且不久,他就会看到十里铺的海了。他有三十年没看到海了。解放前他在广州看过海。海是什么样呢?他已回忆不出了。周庄除了平原和那些常年如一日的大豆高粱、玉米和花生、红薯和芝麻,连一条河流都没有。
“你还在生解放的气吗?”奶奶小心翼翼地说,“其实草莓的死也不怪解放啊。”她的手贴着爷爷的后背,“是草莓小心眼……这丫头属蜻蜓的,从小就小心眼,你又不是不知道,”奶奶知道爷爷没听到她说话,“她让解放找文教局的人疏通疏通,解放没答应,解放也是个死心眼的人……可他是你儿子,你不能老躲着他吧?”
对于爷爷由于生理原因造成的寡言少语奶奶只有叹气。当奶奶和爷爷路经小屯时再次受到了威胁。过了小屯就是县城了,奶奶想到了县城后,她就和爷爷找解放,在解放那里住上一宿,第二天就回家。奶奶养了一群鸭子,还有两只母猪。它们同样是她的心肝宝贝。这时爷爷突然说:“我们先去趟药地村吧。”
爷爷的话让奶奶狐疑。“干吗去药地村呢?”
“你跟我一块去就是了!问那么多干什么?!”
奶奶最忍受不了的就是爷爷对她不尊重。奶奶说:“要去你自己去吧!我是没精力和你瞎折腾了!我去县城看兆生。”
奶奶下了爷爷的自行车,自己蹲在马路边上喘气。爷爷下了车,朝她挥手。爷爷总共挥了三手,他挥手的动作像是一个长官在不耐烦地招呼一个士兵。奶奶当然不吃他那套。爷爷挥完手后,径自上了自行车。奶奶看着爷爷的自行车在路边拐了一个弯道,马上就失踪了。奶奶望着他的背影,心头被马蜂热烈饱满地蛰了一下。
4
奶奶的腿开始隐隐作疼。她感到凉丝丝的水珠舔着她的脸。她已经步行了五里路。她觉得腰都快折断了。她已记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走路变成一件费力气的事了呢?奶奶年轻时,是村里跑得最快的女人。她跑得快纯粹是练出来的,二十几岁时是跑日本鬼子,她背着她短命的妹妹一口气跑了十五里;三十几岁时是跑国民党,她背着一个解放军从周庄跑到夏庄。解放后她就不跑了,唯一的一次是年,和爷爷打架,爷爷拿着把镰刀要割她的耳朵。她偷了公社的包米。可是不偷东西,老闺女能活下来吗?老闺女天天拱着家雀脑袋吮吸她的乳房,都四十岁的女人了,哪里还有奶水?党员怎么了?党员也得喂孩子啊……
那辆卡车在奶奶身边停下来时,奶奶嘤嘤地哭起来。老闺女是年没的。在奶奶的记忆中,她干瘪的脑袋顶着一双瘆人的大眼睛……也只记得那双由于饥饿而惊恐的眼睛了……像老牛被屠宰时的眼睛……悲伤的事总是集体爆发,这样,奶奶又想到了她的二小子。想到二小子时奶奶的哭声大了起来。二小子大串联那年搭火车去了南方,后来就定居广州。他只是每年春节回趟家,给他们带回些亚热带水果。他在动物园当大象饲养员。他当了二十年大象饲养员,后来在一次动物表演中,被一只发情期的母象踩碎了肚子……这孩子一辈子没结婚,无儿无女,最后死在大象手里,奶奶每次想到他,就会记起他赶着生产队的猪去放圈的样子。他从小喜欢动物,他总是吸溜着鼻涕,走起路来轻得像鬼……她再也看不到他们了……他们都死了。有时她把手指展开,她能隐约窥视到孩子们的眼神,在田螺般的指纹里飘来飘去。她知道他们想她。
哭着的奶奶看到卡车上走下来一个男人。她看到这个长着络腮胡子的男人张开嘴巴,龇着一对大板牙嗡声嗡气地问:“大妈,您老这是去哪儿啊?我拉你一程啊?”
当爷爷浑身湿淋淋地到达县城时,已经是中午了。他的那双绿胶鞋灌满了雨水,吧唧吧唧的蹬车声让他很开心。他还看见谁家的孩子在雨中追逐嬉笑。偶尔黑色的轿车呼啸着从身边蹿过,再仿佛一只小昆虫消失在蒙蒙雨气中。楼房已经多了起来,犹如一座座水库孤独地矗立着。多年不见的县城他都不认识了,那些间隔闪过的广告牌让他觉得异常陌生。然后,在那个三角地,爷爷看到一个女人站在一家酒店的屋檐下,朝他机械地挥舞着手臂。
奶奶和爷爷在一家酒店胜利会师。奶奶看到爷爷浑身精湿的模样,竟然笑了起来。她帮他把那辆老水管自行车靠上酒店外的电线杆,对他说:“我们先在这间大房子里躲会雨吧。”
她没问爷爷到药地村做什么。爷爷的白眉毛上粘挂着雨水,奶奶就伸了胳膊替他擦掉。爷爷嘿嘿地笑着,他好像猜到她早晚会在这里等他似的。
酒店外停着不少的轿车,酒店里的人却很少,奶奶不晓得这些人都藏哪里去了,只是时不时地传出酒令的吆喝声。奶奶看到一个漂亮的姑娘走过来。她皱了皱鼻子,问道:“你们吃点什么?”
奶奶不识字,摇摇头说:“我们不饿,什么都不吃。”
姑娘愣了会说:“不吃饭来这里干什么?”
奶奶说:“我们歇歇脚啊。有水吗?给我们倒点水吧。”
姑娘冷笑着说:“原来是要饭的啊?”
奶奶说:“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啊?”
姑娘说:“你让我怎么说?你们这样的人我见识得多了。要饭就要饭吧,还不好意思承认。走吧走吧,我可没时间招待你们。”
奶奶说:“我们等雨停了再走啊。”
姑娘又冷笑了一声,“你们走吧,待在这里影响市容市貌。”
爷爷就是这时候抓起一个烟灰缸砸向地板的。铿锵的声响不仅使姑娘吓了一跳,也使奶奶哆嗦了一下。奶奶还在发愣的空当,那个姑娘脸色刷白地喊了一嗓子。还没等奶奶反应过来,两个穿警服的小伙子已经像猎犬一般扑过来。奶奶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当初对付国军还是满有一套的。但是无疑这是两个办事干净利落的保安。奶奶眨眼的工夫他们已经抓小鸡一样把爷爷和奶奶拎了起来,然后,等他们明白过来时,他们发现他们的身体已经到了酒店外边。
他们看到大街上的汽车乌龟那样缓慢地爬行着,雨是越来越大了。他们茫然地回头看酒店,里面隐隐传出音乐声。爷爷和奶奶是一起冲进酒店的,那一刻奶奶的腿也不疼了,她仿佛又回到了多年前,她的身板杨树般笔直,常年哮喘的喉咙在瞬息变得清脆无比,而爷爷呼哧呼哧着喘气,眼珠子似乎就从眼眶里滚出来。他听到奶奶苍老尖锐的喊叫声:“你们是土匪啊?!哪里有这么欺负人的呢!”
那两个保安面无表情地冲过来时,奶奶看到他们的手里多了件东西,奶奶知道那玩意叫电棒,她看电视时,经常发现这东西被警察同志攥着,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奶奶下意识地拉住爷爷。爷爷的身体还在向前倾斜。奶奶的脑袋一片空白。就在这时,她听到一声亲切温柔的呼唤,“大爷大奶!你们怎么来了?”
这声音让奶奶预感到遇上了亲人。她注视着那个朝她微笑的女人。那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嘴唇红红的,穿着件露肩膀的套裙。
“我是秋秋啊!”那女人操着一口东北话说,“我是赵大年的女儿秋秋啊!你们真是上年岁了,连秋秋都不认识了。”说完她咯咯地笑起来。奶奶极力回想着这是哪家的孩子。爷爷突然说话了。他说:“秋秋,你不是在服装厂上班吗?”
奶奶这才想起来。这个秋秋正是周庄赵大年的闺女。可赵大年的闺女怎么说东北话呢?秋秋说话的时候,她后面又鸟悄着蹑上来个男人。这个男人眼神呆滞,明显是喝了不少酒。秋秋转身趴在男人耳蜗上嘀咕着。男人脸色变了变。“你们过来!”他挥挥手,那个长雀斑的姑娘和两个保安乖乖地上前,“你们怎么这么对待两个老人呢?这不是破坏我们酒店的形象吗?”
看着保安低三下四地顺着眉眼,奶奶倒有些不忍,她说:“饶了这几个孩子吧,他们小,不懂事呢。”
男人笑了笑说:“是,是。他们哪里知道你们是周局长的父母呢?我待会给周局长打个电话,向他赔礼道歉。我们是有眼不识泰山啊。”
秋秋也说:“你们吃点什么?我叫厨师做啊。”
奶奶看到男人的手在说话的时候不时地摸一下秋秋的屁股。她觉得这不可思议。秋秋不是找的夏庄的婆家吗?怎么倒和这男人猫三狗四的。她叫秋秋过来说:“秋秋啊,别做傻事啊。到时候后悔来不及。”
秋秋尴尬地笑了笑,“瞧奶奶说的。我是酒店里的领班。我早不在服装厂上班了。”
奶奶和爷爷离开酒店时,经理和服务员毕恭毕敬地送出来,奶奶和他们热情地摆摆手,然后她凑在爷爷身边说:“这个让人不省心的丫头,什么时候改说东北话了啊?”
(短篇节选)
选自《长江文艺》年第7期
原刊责编:向午
本刊责编:鄢莉
《长江文艺·好小说》年第1期
—END—
《长江文艺·好小说》年第1期目录
自在说孤单的旅程
张楚
再发现旅行
张楚
草莓冰山
张楚
那些不曾被遗忘的
时光(创作谈)
好看台中篇
虎妹孟加拉
陈谦
三只铁碗和三只汤勺
尹学芸
一树荒原
王甜
短篇
大宴
鲁敏
我们在深夜里长谈
曹军庆
活在尘世太寂寞
哲贵
一场撕心裂肺的出轨
武歆
推手推毕斯先生的怜爱
陶丽群
青春季Munro小姐
白琳
再回首另类生存:方力钧手稿研究展
傅中望
翠柳街多元的文学格局更有活力
喻向午
《长江文艺·好小说》年第1期
—END—
长江文艺杂志社
《长江文艺》邮发代号38-6
每月单本定价10元,全年定价元,每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