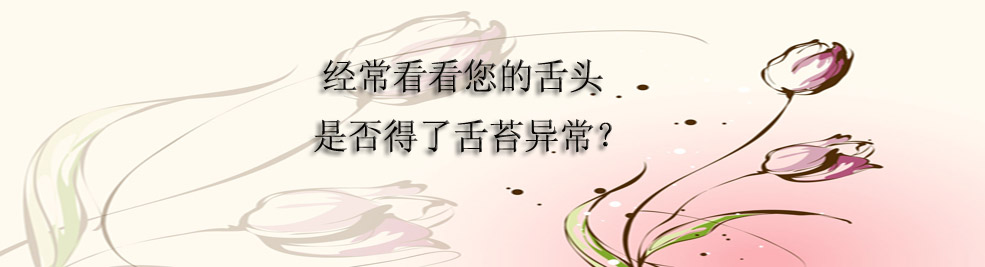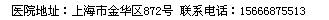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舌苔异常 > 饮食护理 > 山花年第7期冯桂林绅士
山花年第7期冯桂林绅士
冯桂林,上海人,年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年顶替回沪进上海人民服装一厂。年辞职,移居香港,开始经商,年定居美国。年退休,开始文学创作,在《山花》发表处女作《偷渡者》。
冯桂林
1如果我不是遇到戴斯年,我永远也不会懂得绅士和男人的区别。
戴斯年想为他们家族公司旗下的五星级酒店的员工订做制服,通过我的朋友邹宁找到我香港湾仔的金丰有限公司,秘书把他领进我的办公室。
戴斯年给我的第一印象实在太差。五短身材,五十岁不到的年纪已经头发花白,高度近视的眼睛在啤酒瓶底厚的眼镜后面眯成一条缝,白衬衫裹着的大肚子从黑西装中间挺出来,像一只企鹅。
“我系戴斯年,我揾冯生。”他先开了口,很有礼貌。
“你好!我系冯生。”我伸出了手。
“你好!你好!”他接过我的手握住,怔了一下,“你边度人啊?”
“我系上海人。”
他突然甩开我的手:“喔唷,大家上海人,讲啥头命的广东闲话?”我俩一阵哄笑。
他递上名片,我一看:香港戴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戴斯年,副董事长。
戴氏实业是香港家喻户晓的上市公司,我抬起头重新审视着戴斯年。戴斯年连忙说:“公司老板是我大阿哥,我们家六兄妹,我最小,只好做点跑腿的事。”
戴斯年一挥手说,做制服这种事交给下面的人去做,我们吃饭,白相。
我们约了晚上六点半在铜锣湾洛克道的富豪饭店吃饭,我从公司坐地铁过去只有一站路。我掐准时间到达时,恰好一辆奔驰敞篷车在饭店门口停了下了,戴斯年从驾驶位下来,急匆匆越过车头,打开副驾驶位的车门,一个女人搭着他的手下了车。戴斯年把车交给泊车侍应,用手指点了点挽着他手臂的女人向我介绍:“江雨桐,我的女朋友。”我们互相问了好。
江雨桐,看上去三十岁不到,不对称的过耳短发,一边向前盖住半个眼睛,另一半却掖在耳后,姣好的面容若隐若现,令人想一探究竟。她穿着珍珠白的无领套装,碳灰黑的滚边镶嵌在领口、袋口、袖口、脚口、门襟,白不耀眼,黑不极致,她脚蹬白皮黑跟的高跟皮鞋,我领教了香港女人的品位。
江雨桐看上去比戴斯年高了半个头,气场却盖不过丑陋的戴斯年。我们一进门,侍应们立即围上来,异口同声喊道:“戴生,晚上好!”戴斯年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双手抬起,就有侍应把他披在西装外的风衣从背后脱下拿走。
侍应把我们领到桌子边,江雨桐走向桌子的同时戴斯年已经把椅子搬后一步;江雨桐坐下的同时戴斯年已经把椅子向前一步送到她屁股底下。
我们三人坐定,侍应躬身问:“戴生,今日食点咩吔?”却不提供菜单。戴斯年说了句:“都系自己人,简单嘀。”算是点完了菜,戴斯年把这儿当自家饭堂了。
侍应拿了瓶红酒过来,倒入醒酒器。我拿起酒瓶,看那标牌“奥比昂酒庄,”,我问:“为什么选年呢?”戴斯年说:“年是法国波尔多地区天气最出色的年份,所以品质最佳。”现今是年,这沉睡了十三年的红酒在醒酒器中与空气接触后苏醒了过来,此时已经芬香四溢了。
侍应给我们每人杯中倒了一撇酒,我拿起水晶杯晃了几下,在灯光下,杯中那晶莹剔透,犹如红宝石一般的液体宣示着酒红色的高贵。
戴斯年举杯:“冯先生,来,为我们相识干一杯。”江雨桐也举杯对着我,我慌忙中把酒杯送上去,水晶杯轻轻相碰,“咣”“咣”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我喝了一口,让酒浸没舌苔,红酒的果香甜涩的味道在舌尖处蔓延开来,酒入肚,有股醇厚通过血管升上头,脸上微热,果然好酒。
戴斯年一饮而尽,把空杯放在桌上问:“冯先生来香港几年了?”“五年了,可是广东话还是讲不准,让你一听就听出来了。”我自嘲完问:“你的广东话讲得很地道,你来香港几年了?”戴斯年略一沉吟说:“有十几年了。”“家人呢?”我接着问。戴斯年说:“老婆老早离婚了,女儿在加拿大读书。”
我扫了一眼江雨桐说:“哦,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戴斯年也看向江雨桐,见江雨桐正冷眼斜视他,便移开目光,说:“这不急的咯,等两年吧。”我觉察到了微妙,便刹住话头,举起杯底的剩酒说:“来,我敬你们两个。”大家目光又回到了拿起的酒杯上,江雨桐一仰脖子,率先把酒倒入喉咙。
冷菜上来了,每人一小碟,碟中有卤味三拼和三蔬,分别是鸭胸、鸭掌、鸭胗,冬笋、莴笋、芦笋,每样只有两小片。要放在平时,我用筷子往嘴里一扒拉,也就一口闷,现在也只能学着他俩一片一片数着吃,还时不时地放下筷子,用餐布在嘴唇上碰一碰。
上例汤了,侍应将瓦罐搬上桌,用勺子伸进去将汤滗出,每人分一小碗,看着他俩喝汤用小调羹一下一下送入嘴中,我实在嫌费事,便端起碗一口喝完。
戴斯年喝了半碗汤,把调羹放在一边就不再喝了,头转向我说:“听邹宁说,你白手起家,生意做得不错,早就想认识你。”我回道:“做服装呀,小生意,不能和你们公司比……”“哎!”他打断我,“你不能这么说,香港上市公司利丰,ESPRIT都是做服装的。”他摇了摇头又说:“我们公司再大,也是大哥的,我早晚要自己独立出来,到时再向你请教。”说着举杯和我单独喝了一杯。
我又瞧了一眼江雨桐,觉得冷落了她,正好江雨桐把挡住眼睛的头发往后拢了拢,我才一睹庐山真面目。她天生长眉,丹凤眼,鼻梁挺括。她举止得当,坐姿优雅,静听着我们讲话,从不插嘴。
主菜上来了,每人一个四头鲍鱼。饭店经理亲自端上来,说这些日本吉品鲍是他们饭店的箱底货,专门招待贵宾的,一般客人只供应南非干鲍。经理为每个人摆好了刀叉,说了声慢用,就退去了。
戴斯年的刀功竟然比江雨桐还好,能把鲍鱼切成云片糕一样薄。我则切成三大块,用叉顶着,一小口一小口啃,鲍鱼糯黏韧弹,是任何鱼肉无法比拟的。吃在嘴里,反复咀嚼,不舍下咽。
戴斯年叫了每人一小碗白饭,随饭上来一盘白灼生菜,我学着他用鲍鱼汁拌饭,鲜美无比,竟还想来一碗,可惜鲍鱼汁没有了。
江雨桐没有吃饭,只吃了几片生菜。
饭毕,每人一份水果,西瓜、蜜瓜、木瓜、哈密瓜,各一片,四种不同的颜色,切成同样大小的尺寸。
这时,江雨桐起身,说了句上化妆间。戴斯年看着江雨桐离开的背影,转头对我说:“结婚做啥啦?好不容易离婚,再弄个人回来管着我啊?”他把椅子搬了靠近我问:“你离婚了吗?”“没有啊!”“那你有女朋友吗?”“没有啊!”戴斯年瞪大眼睛看着我,用手指频频点我:“你白活了。”
戴斯年用手掌指向桌子上的空碟说:“鲍鱼好吃,天天给你吃,你要吃吗?不要吃的呀。”他自问自答后,用手背在我的胸口敲了几下说:“女人要换的呀!”
侍应拿来了账单放在桌上,戴斯年看也不看要签字,我抢了过来说:“我付吧。”戴斯年说:“他们不会让你付的,他们月底向我们公司结账。”我看了一下账单,一万七千元,脱口说:“吃顿晚饭太贵了吧?”戴斯年不以为然:“钞票赚了做啥?不就是要享受生活吗?”说完,他偷瞄了一下左右,把脸凑过来,用手捂住嘴唇,压低声音说:“各种女人味道不一样的!”
江雨桐出来后,我们便离开了饭店。在分手时,戴斯年说:“翡翠戏院明天上映好莱坞大片《虎胆龙威》,我们一起去看晚上七点档的?”我说好的。
第二天,下班后。我在公司吃了一个四宝饭的盒饭,又是坐地铁一站路到了铜锣湾的翡翠戏院。我第一个到,接着江雨桐也到了。她今天穿一袭露背粉红色连衣裙,背一个暗红色的方形包,脸上淡妆,却烈焰红唇。她见我的目光在她的身上打转,便问道:“好看吗?”“嗯,好看,就是这个包不好看,皮质粗糙,款式古板,色彩暗淡,应该换一个靓丽一点的。”她低头看了看包说:“爱马仕就是这个风格。”我说:“没听说过,我只知道LV包是最好的。”她莞尔一笑。
戴斯年一直没到,打他手机也不接,不知发生了什么?直到电影开始放映了,江雨桐说算了,不等了,我们进去看吧。
电影一开始就是纽约第五大道酒店爆炸的火爆场面,我们被吸引了。接着,布鲁斯·威利斯挂着牌子站在黑人区,脸上露出招牌式的忧郁深沉的表情。江雨桐在黑暗中用胳膊碰了我一下,在我耳边说:“其实,你的神情和他很像,我喜欢深沉的男人,酷!”
继续看电影,半小时后,我发觉江雨桐低头睡着了,我推她:“怎么睡着了?”她却眼也没有睁,说:“借你肩膀靠一靠。”说着把头靠在我的肩头,调整好坐姿继续睡。
我的脸颊摩挲着她的头发,久违的发香和她的鼻息直冲我脑门,我一阵晕眩,无心看电影。电影快结束时,她终于醒了,她坐直身子,重重地吸了一口气,抹去流下的口涎。我问:“你怎么了?昨夜没睡?”她说:“让他折腾了一夜,这个变态佬。”我不敢再问下去了。
出了电影院,正下着雨。她从包里拿出折叠伞,撑了起来,我们并肩往的士站走去。她见我在伞外淋雨就说:“进来啊,淋雨干什么?”我说:“雨不大,没关系。”她不容反驳地说:“过来!”我靠了过去,保持着距离,两个人都有半个身子淋到雨。她用胳膊撞了我一下嗔道:“让女孩子帮你打伞啊?”我慌忙接过雨伞,她腾出来双手抱住我的胳膊,两人都挤进了雨伞。我的胳膊深陷在她胸前的两团肉中,两面夹击的柔软使我顿时呼吸急促,步履艰难起来。但我立即把那一点欲望的火星给掐灭了。朋友妻不可欺,这是不可触碰的底线。
2戴斯年告诉我戴氏集团将在周六晚上七点,于湾仔会展中心举办成立30周年庆典,邀请我参加,香港上流社会很多名流都会参加。
这天下午,我特地去了金钟太古广场买了一套皇家御用的KENTCURWEN牌子的西装,两万多元,原本不舍得花这么多钱,但是,自那天富豪饭店一万七千元的晚餐后也就想通了。
晚上六点半我就到了会展中心,刚在门口桌上的签到簿上签了字,就碰到了戴斯年。他把我领进偏厅的沙发上坐下,侍应已经一只手托着盘子走上来,一只手放在背后。戴斯年从托盘众多高脚杯中抽出两支香槟酒,说:“今天的场合应该喝这个。”我喝了一口这种黄色的葡萄酒,满口苦涩,皱起眉头。戴斯年说:“这是二次发酵的气泡葡萄酒,香槟地区出产的才能叫香槟酒,其他地区只能叫气泡酒,你喝几口就会习惯的。”
我正想起身去拿杯橙汁,戴斯年把我按下问:“那天看电影怎么样?”“电影很好看,你怎么不来?”我说完这句话,想起江雨桐头靠我肩膀睡觉和同撑一把雨伞,有点心虚。戴斯年暧昧地笑着:“我存心不来的,为你们俩创造条件,你喜欢她吗?”我愣住了,心中快速猜测戴斯年的用意:试探?警告?然而,我在戴斯年的眼神中分明看到了诚意,我以攻为守:“你帮帮忙好吗?朋友妻不可欺的。”戴斯年的眼神一下子变得认真起来:“你以为你在水泊梁山啊?还朋友妻不可欺呢?现在已经是换妻的年代了。”
我脑袋一片空白,戴斯年的脸上又出现了诚意:“就算你帮我忙好吧?这个女人已经跟了我三年了,现在吵了要结婚。”
我正无语间,戴斯年突然恭谨地站起来。他大哥进来了,身边跟着穿黑西服戴耳麦的保镖,他大哥叫戴斯礼,是港督授勋的太平绅士,70岁,身材偏高,不像戴斯年。一件毛麻混纺的麻灰色西装,经过拔烫工艺和体型严丝合缝,就像蝉蜕下的壳和蝉那么合身,脖领围一条丝巾,白裤子白皮鞋,时髦而不失庄重。再看一眼我的传统西装套就显得土气了,就像香港房屋中介的打扮。
戴斯礼走过来和我握了一下手,我连忙叫:“大哥好!”其实,他年龄比我爸还大。戴斯礼用已经生疏的三十年代的上海话说:“侬是小弟的朋友,来捧场交关感谢!”保镖把从耳麦中收到的信息告诉戴斯礼:“湾仔警署署长查理到了……噢,霍英东到了。”戴斯礼和保镖说了句话又转向我说:“今朝人霞企多,怠慢了,小弟陪陪。”说完话转身走了。
我完全被这位超级富豪的气派和太平绅士的风度征服了,虽然他只和我讲了两句话。我决定,要像他那样友好地对待每一个认识的人。
我和戴斯年走进大厅,有一二百人之多,人们手里拿着高脚杯或者雪茄,三五成群地交谈、寒暄。我感到一种压力,我不配这种场合,不敢走进去融入人群,再说,我的广东话别人一听就是“新移民”,港英时代的香港人鄙视北边来的“表叔”。戴斯年虽然广东话比我好,但他的身份必须冠上“戴斯礼的弟弟”才行,他也不想走入人群。
我俩坐在大厅边上的沙发上,戴斯年指着大厅的人群说:“这些香港赤佬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比我们早到香港,其实,上海人比他们聪明多了,不会输给他们的。”我向戴斯年投去敬佩的目光,没想到,他竟如此自信,比我强多了,我比他小,真可以把他当兄长。戴斯年继续说:“我大哥同意我从家族公司分出一部分医疗器械生意,我已经做了几年了,我一定要让我自己的公司上市。”听到这里,我已经对戴斯年从敬佩变成敬仰了,我转过身来,正对戴斯年的侧身,像学生聆听导师的教诲。
戴斯年见我听得认真,便也转过身来说:“其实你也可以上市的。”我吓了一跳:“我哪里行啊?”戴斯年摊开手掌扫了一圈人群:“其实,他们中的一半人,生意还不如你呢,做生意不能死做,上市,资产能翻几倍,去白相人家的钞票。”我依然不开窍,说:“就凭我公司现在的规模,上不了市的。”戴斯年开导我:“这有什么关系?业绩都可以做的啊,上市就是要讲故事,讲一个骗得了人的故事。”
戴斯年想了想说:“这样,明天我叫毕马威的董事耿先生出来一起吃饭,把你的公司包装一下,毕马威知道吧?世界四大会计师楼。”
我摇摇头,我真不知道。我觉得,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有点自卑。我把侍应招过来,拿起一杯苦涩的香槟酒,一饮而尽。
晚上,我回到炮台山的家中,戴斯年的话如同在我的脑海中扔下了一颗石头,掀起了巨大的涟漪,一圈一圈扩展开来。我没有想到,生意可以这样做。我坐在落地窗前看着维多利亚港美好的夜景,近处是大楼的灯光、霓虹灯、渔火。很远的地方是一片黑暗的虚无,然而,能看到一闪一闪的灯塔的光。
如果戴斯年关于生意上的话题只是在我的脑海中投下了一颗石头的话,那么他关于女人的话题却是把我内心深处封闭的地壳打破了,对女人的欲火就如同火山爆发一样不可收了。
我不得不承认,戴斯年关于女人的话讲得有理,我也不得不承认江雨桐对我有吸引力,但,我无法确定江雨桐是不是对我有意思?仅凭她头靠在我肩上还有把胸顶着我胳膊?
这一夜,我彻夜未眠。
请毕马威的耿先生吃饭,当然也包括戴斯年和江雨桐,我可不想在富豪饭店吃得那么“简单”,我选在了铜锣湾的富临海鲜火锅饭店。
我和戴斯年、江雨桐一起走进饭店,饭店足有两千平方米的大厅里桌桌爆满,人声沸腾。我们之间讲话也要大声喊才能听到,我看到戴斯年皱了下眉头。
我自己去海鲜池点菜:一条两斤的东星斑、一斤基围虾、烧味拼盘、烤乳鸽、大鲍翅、焗龙虾……,总共才三千元。我挖空心思想点得丰富些,可是,饭店服务生说:“够了,吃不了的,先点这些吧。”
我们刚坐下,耿先生也来了,耿先生和我一样,穿着西装套装,香港人,四十岁左右。戴斯年帮我们介绍过后就和他一直谈事情,看得出他们很熟。江雨桐今天穿米色雪纺长衬衫和黑色紧身裤。
戴斯年说今天喝啤酒,服务生把啤酒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我们自己把酒杯倒满,先干了一杯,吃了一点上来的冷菜,就进入了正题。
耿先生问了我公司最近三年的生意额和利润情况后说,要到我的香港公司和上海公司看全部的财务报表,我同意了。耿先生告诉我上市的前期费用要两千万元,包括审计、包销等所有费用,我也同意了,这是行情。戴斯年说如果上市成功,他要占百分之十的股份,是他和耿先生的,我没有同意,要讨论。
我们三个人就像工作晚餐,桌子上放满了一些上市的文件,没顾得上吃菜。江雨桐一个人在喝闷酒,我看到她脸上的红晕已经延伸到了脖颈,也许是酒的作用或者是被长时间冷落的原因,江雨桐一反常态竟在饭桌上插嘴了:“我说,吃饭可不可以不要谈工作?”戴斯年像不认识江雨桐一样看着她说:“你不要听,你回去!”“回去?你需要我时就当我是工具,不需要时就半个月不理我,我跟了你三年,这种日子过够了!”江雨桐把啤酒杯重重地放在桌子上,杯子里的酒溅到了文件上,耿先生拿纸巾来擦。戴斯年一拍桌子:“过够了就分手,我也过够了呢。”
我和耿先生尴尬地坐着,江雨桐拿起酒杯,一口喝下去,来不及下咽的酒顺着嘴角流到衣服上,然后,拿包起身就走。戴斯年怔了几秒钟,对我说:“去追她,把她送回去好吗?”
我追了出去,江雨桐果然喝多了,出了门,没走几步,就蹲在路边吐起来,等她吐完,我拦了一辆的士车,把她送到家里。
一进门,江雨桐说:“我没事了,你走吧。”“那你自己当心。”我说着走到了门口。江雨桐改变了主意:“你别走,陪我说说话。”我又回到屋里,我乘势走着看了房子,两室一厅,有一百二十平方,在香港算是大房子了。
我俩在三人沙发上坐了下来,江雨桐说:“今天让你看笑话了。”“酒喝多了很正常啊。”我宽慰她后又恭维她,“房子不错啊!是戴斯年买给你的?”“屁!”江雨桐被激怒了:“他买给我?这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妈已经去世了,爸再婚去了加拿大。”“对不起,我不该问你私事。”我突然觉得我八卦,怎么问这些?说明我在心里北京看白癜风哪个医院专业北京中科医院在哪里